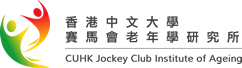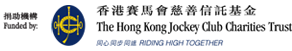赛马会安宁颂
安宁服务培训及教育计划
个案:张女士
透析治疗的抉择
张女士是一名75岁的独居病人,曾接受腹膜透析的治疗。她因为中风的缘故出现了偏瘫和认知受损的问题,所以不能自行处理腹膜透析程序,而家人亦未能提供协助。张女士因为拥有一定资产,不符合申请综缓的条件,而她的子女亦无足够的负担能力让她入住能提供腹膜透析治疗的老人院。张女士亦因为迷惘和认知受损的问题而长期尝试拔出腹膜透析导管,因而须要接受24小时的约束。现在张女士已入住复康医院长达数个月了。在这个案中,医护团队应如何处理她未来的医疗及照料?相关的道德衡量又是什么?
—————————————————————————————————————
沙田医院老人科专科顾问林楚明医生撰写
较年长病人每每多病缠身,这方面与年轻病人通常只患有单一病症大为不同。临床管理单一疾病的决策一般简单直接得多。然而,当多种情况同时出现,制订护理计划时便需采用一套综合的全人方针。
以张女士的个案为例,她本来只患有慢性肾衰竭的单一病症,曾接受肾脏替代疗法,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即使独居也能在治疗后自行管理腹膜透析。可是张女士后来中风而且认知受损,这种残障令她无法再独自居住或自行管理透析治疗。张女士曾多次尝试拔出自己的腹膜透析导管,须要使用身体约束。临床团队当时很可能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应否继续采用该肾脏替代疗法(善行)。由于张女士依赖肾脏替代疗法,假若把疗法撤走,是否等同于主动进行在香港属于违法的安乐死(伤害)?她住院已有很长时间,这对于其他等候复康服务的病人又是否公平(公义)?应该向张女士的家人建议怎样的整体护理计划?
就公平相关的问题,也许是上述问题中最容易回答的。当医生与病人建立了关系,为医者便须肩负照顾责任,就像张女士的个案一样。虽然资源紧绌,「放弃」张女士而不安排合适的护理是不道德的做法。根据香港《精神健康条例》,市民可以透过监护委员会提出申请委任一名正式的监护人在若干限额内处理个人财政,以及处理其居所和接受医疗护理的决定。虽然张女士的资产很可能超过获委任监护人可作决定的限额,但她的家人可以引用条例第II部份,把有关资产透过高等法院出售来支付她未来的医疗护理计划。由于完成这项程序可能需历时多月,医院管理层和社会福利处有需要进行高层次对话,在达成最终决定前安排中期出院安置。
过去数十年来,善行、不伤害、自主和公义,都是医学伦理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支柱并没有先后次序之分。那么,如果其中一项支柱和另一项互相矛盾(像张女士的个案,善行和不伤害两个原则产生对立),又该如何处理?近年在医学伦理上建议采用一套新的方法,从考虑医疗合适性、病人的选择、生活质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来考虑及作出最合适的决定。
要评估医疗合适性(医学方面的善行和不伤害),需要采取一套综合的全人方针。正如张女士中风前的情况,腹膜透析治疗令她受益,提供了更高的生存机会并减轻慢性肾衰竭的症状。然而,腹膜透析治疗的好处,很可能会因为中风后身体功能大受限制而衰减。虽然我们不知道张女士身体机能的详细情况,但她很可能属于体弱个案,这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预期她跌倒、住院甚至死亡的机会比没有体弱的人为高。此外,她须要受约束,而且容易因住院患上各种并发症,包括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失禁、易受感染和与压力相关的皮肤损伤。另外,她尝试拔出腹膜透析导管也降低了治疗的效用,
而且会带来内脏撕裂和腹膜炎的风险,这些都是伤害的重要元素。总的来说,腹膜透析治疗对提高存活及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而代价是重覆的创伤和不适(在心理和生理上)。平衡两者和观乎现有资讯,现时继续使用腹膜透析治疗和约束病人的医学介入整体好处非常有限。当然,假若张女士在身体机能和认知上有重大改善,令其不再需要受约束和不会拔出腹膜透析导管,这个平衡或会倾向于集中进行腹膜透析治疗的医学介入。
在个人选择方面,张女士的认知已受损,无法作出合逻辑的判断或决定。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她此前有没有就预设医疗指示或预设照顾计划做过决定。即使这样,现时的预设医疗指示或预设照顾计划表格并没有就「指定情况项目」分类(例如是否使用腹膜透析)。然而,如已备有预设照顾计划,而计划经妥善执行,记下了病人的价值观、偏好、生活上最不能忍受的身体状况等资讯,便可以为她的个人偏好和选择提供指引。以张女士的个案而言,我假定她并没有预设医疗指示或预设照顾计划,大家便需要与张女士的家人讨论她此前有没有就临床管理表达过任何目标和偏好,还有她有没有提及过认为无法接受哪种身体状况。
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生命价值观,难以一概而论。即使如此,有些领域是共通的,例如是尊重、尊严、自由,和不接受痛楚/不适。尽管我们无法和张女士进行有意义对话,从她不断重复拔出腹膜透析导管的做法可见她因为这样感到不适。她的做法,往往被人冠以医学上的「迷惘」或「神智不清」,因而以约束衣来避免她的「自损」行为。她的「自损」行为,是否只是为了移除令其感到不适的腹膜透析导管所产生的自然反应?使用身体约束来阻止拔管行为,又是否令她感到更不适和更痛苦?不适度的约束可令即时伤害更严重和牵连更广,这又是否合适?如果把生活质素的因素纳入医疗合适性的决定内,则持续使用腹膜透析治疗会造成的伤害比医疗得益为大。
就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由于病人此前曾接受持续的腹膜透析治疗,有人可能会担心不继续腹膜透析治疗便等同于主动安乐死。在香港,安乐死﹙主动采取行动提早结束生命﹚属刑事罪行。但就病患者因生命已到达医疗上不能逆转的情形下,不作出令病患者更不适的无效治疗而自然死亡是可以接受的。香港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人们非常注重家庭关系,决定往往会考虑对家庭的影响,而不只是个人因素。建议多聆听家人的想法,并与他们达成共识。
总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张女士会否在身体机能和认知上能有明显改进,令她能够安全地接受腹膜透析。我们应采用一套综合的全人评估方针(而不是只采取医学或个别疾病的视角)来与病者的家人坦诚讨论病情,包括张女士对生活质素的看法,此前有否就临床管理的目标表达过任何意愿,然后基于以上各因素提供建议,并与家人达成共识。在情况不明确的时候,亦可以尝试作出治疗,观察实际效果。在张女士的个案上,假设身体改善已没有特别进展,大可建议有限度约束身体(例如只用手套)来避免她拔出腹膜透析导管。如果做法成功,便可以乐见在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约束下生命仍得以继续。此前提及有关监护委员会/高等法院的资产管理申请便在这里适用。另一方面,假如张女士再次拔出腹膜透析导管,不把其重新插入而只提供减轻令人难受病征的医治是可以接受的,这还可能更符合张女士的最佳利益。同样地,这决定应与张女士的家人彻底讨论。当医护团队和病患家人同为病者的「最佳利益」作出发,大家便能携手合作,一般情况下都能达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