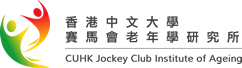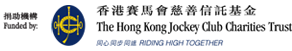赛马会安宁颂
安宁服务培训及教育计划
个案:曾太太
晚晴照顾决定之「孝」
曾太太90岁,曾患心肌梗塞、心房颤动、以及充血性心脏衰竭。自从她丈夫8年前过世后,她一直住在安老院。曾太太盼着女儿嘉欣定期来看她,女儿每次都会从老街坊的烘焙店买来她最爱吃的纸包蛋糕。不过曾太太最想念的还是大儿子嘉杰。嘉杰跟家人住在加拿大,每年大概回香港一次。
去年,曾太太因心脏衰竭病情加重,令她每隔几个月都要住院。每次发病时,她的腿都会肿胀,而且稍微走几步路或躺在床上都会令她喘不过气。住院期间,曾太太接受静脉利尿治疗,排出体液后,她的呼吸才会有所改善。然而,每次返回安老院时,她都愈加衰弱。最后一次出院时,她已感觉到双腿不听使唤,几乎无法站立。
曾太太最后一次出院的两个星期后,社区老人评估小组的护士Ivy探望了她。Ivy注意到曾太太过去几个月里每况愈下、日渐消瘦的情况,于是决定趁曾太太意识清醒时,与她和嘉欣安排会面,讨论预设照顾计划。
会面时,Ivy解释了对于曾太太健康衰退的担忧,并询问曾太太关于后续护理的期望。曾太太回答说:「我知道我情况不好,我只希望不需要经常进出医院。医院的员工总是很忙,没太多时间理会你。」嘉欣点头表示同意,「妈妈最近经历了太多次住院,受苦不少。她真的很不喜欢住医院。」
Ivy随即为她们讲解了她所在医院的晚期护理服务(EOL),可以帮助曾太太尽可能避免住院,并以她的舒适为重。
「我们会定期评估你的健康状况是否有任何异常,并尽可能让你在安老院接受治疗。如果需要住院,我们会尽量安排你直接入住老人科病房,避免前往急症室。参加该服务计划的病人只需同意不进行心肺复苏。换句话说,一旦出现心跳停顿,病人将会放弃让医疗团队采取恢复心跳的任何尝试。」
曾太太一听就紧张了,「如果我心跳停了,我还是希望医生想办法救我!」
听妈妈这样说,嘉欣叹了口气,「这个计划各方面都不错,只是我妈妈还未准备好放弃。恐怕我妈妈的情况不大适合你们的计划。」
Ivy在商谈记录上做了些备注,没有再次提起晚期护理服务。
数月后,安老院的护工发现曾太太昏迷,立刻叫救护车将她送至医院。急症室的医生发现其血氧含量和血压过低。考虑到她出现呼吸衰竭并处于休克状态,医生立即给她戴上无创通气面罩。经过治疗,曾太太的血氧水平有所回升。病情趋稳后,她被转送到内科病房。随后病房的护士致电嘉欣让她立即前往医院。
嘉欣到达病房时,接待她的是曾太太的主诊医生梁医生。他解释说,「我担心你妈妈的情况可能随时变得不稳定。考虑到她有严重的心脏病,整体的健康情况比较差,如果出现心脏停顿,我不认为心肺复苏术(CPR)符合她的最佳利益。」
嘉欣回答说,「几个月前有位护士在安老院跟我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一旦心跳停止,我妈妈还是希望医生能帮她恢复心跳!这是她的原话。我不知该怎么办,医生!让我先跟哥哥商量一下。」
梁医生点头说,「好的,快去吧。决定好了就告诉护士,也可以随时找我。最好今天就做决定,因为情况可能会迅速变化。」
嘉欣立刻打电话给嘉杰,当时加拿大时间已近凌晨3点。幸好,有人接电话。嘉欣说明了情况,并询问哥哥的想法。
「不用纠结,」他说,「虽然你和妈妈跟护士讨论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妈妈自己说希望做复苏,我们做儿女的怎么能违背她的意愿!再说了,如果有办法让妈妈活得久一点而我们不支持,那就是不孝。我坐明天到香港的第一班飞机。等我到了再说,你照顾好妈妈。」
哥哥的话让嘉欣觉得很矛盾。她哥哥好几个月没见过妈妈,不知道妈妈受了多少苦。此外,她也不确定妈妈是否真正明白护士在安老院中提到的心肺复苏术对于她这种病情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她更是无法想像妈妈会病到多么严重才需要这样做。
另一方面,她希望妈妈在临终时能感到舒适和有尊严,因此倾向于同意梁医生提出的不采用心肺复苏术的建议。但她又不想违背哥哥的主张和妈妈先前表达过的意愿。
—————————————————————————————————————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区结成医生撰写
曾太太的女儿嘉欣陷入两难处境。曾太太已失去意识,个案中的医生建议,考虑到其严重的心脏病以及较差的整体健康状况,进行心肺复苏术(CPR)不符合其最佳利益。因妈妈的情况不稳定,嘉欣须在当天之内将决定告知医生。在之前与社区老人评估小组的护士会面时,她妈妈显然已经表达了自己希望通过必要的复苏治疗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愿,但嘉欣不确定在那段简短的对话中,妈妈是否真正明白心肺复苏术意味着什么。她本人希望妈妈能舒适及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而她身在加拿大的哥哥则认为不支持妈妈继续生存的意愿是不孝。
该个案说明,晚晴照顾的艰难决定,例如是否进行心肺复苏术,通常不仅是基于一两个「合理」的伦理原则而作出的「正确」决定。当处于生命末期的病人精神上无能力作出决定时,决定病人的最佳利益(更准确地说是「各方面的最佳利益」-而并非单一维度上的利益概念)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临床预后、对于采取更积极甚或可能激进的医疗介入的利弊权衡、以及病人事先表达过的意愿和已知的价值观。
如果有明确有效且适用的书面文件作为预设医疗指示,则不作心肺复苏术(DNACPR)的决定可能更简单。在该个案中,曾太太先前表达的意愿(继续活下去)反映了那段对话时她的价值观,但并不构成明确的预设医疗指示。无论如何,预设医疗指示应会明确指出病人在未来的特定状态(例如大脑死亡、末期疾病)下不希望接受的医疗介入。即使病人事先表达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心肺复苏术的意愿,医护小组也没有义务一直遵循病人的指示。医护小组的判断也应起到影响决定的作用。
当该个案的医生向曾太太的女儿嘉欣提出建议,即他认为心肺复苏术并非符合曾太太的最佳利益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曾太太先前表达的意愿。但他可以尝试跟曾太太的女儿共同商讨其母亲意愿的背景-例如,其母亲是否完全理解心肺复苏术,以及像她这种病情的预后?也许她妈妈的说法只是表达了对于医生会「放弃」她的担忧,而非作出有心肺复苏术决定的事先指示。
如果是这种情况,则要求嘉欣「决定」是要进行心肺复苏术还是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做法就有问题。这样做会给她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因为这就意味着在如此两难的处境下,她要独自承担「决定」的责任。如果认为病人并没有就心肺复苏术作出事先指示,则医护小组最好提出更明确的观点,并从一开始就说明该决定是由医护小组与病人家人根据病人先前的意愿和价值观达成共识之后,而共同作出的决定。
香港的法律并没有沿用美国的家庭成员代作医疗护理决定的法律框架。因此,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要做的是代作决定—即是想像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假如病人有能力表达其观点时会想要如何处理。代作决定的概念可以很复杂,很多非专业人士(可能也包括医护人员)在实践过程中会发现不少的困难。
我们注意到,曾太太的儿子立即从加拿大乘坐飞机回来。如果病人情况允许,最好在他回来后进行家庭会议,以便详细告知他曾太太当前的病情以及预后。
如果曾太太的情况迅速恶化、出现心脏停顿,并没有时间作出共同决定,又该如何?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去判断曾太太的临床预后,包括进行心肺复苏后,她能否撤去呼吸机。从已知的资讯来看,我们并不清楚曾太太的情况是否属于无效用治疗(狭义上的生理上无效用的治疗),进行心肺复苏术可能仍然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则应给予嘉欣适当的辅导和支援,以减轻她对于不孝的负罪感。
最后,可能要注意的是,最初提供给曾太太和嘉欣关于直接入住老人科病房计划所需「条件」的资讯是可以斟酌。该计划可能确实是专为那些在订立预设照顾计划时,就已经表明不接受心肺复苏术的病人而设计的,但如果病人只是出于尽量舒缓不适的目的而选择直接入住老人科病房,而他/她却因此被「要求」同意不作心肺复苏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良好的晚晴照顾计划不应将其服务作为「诱因」,从而影响病人作出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决定。我确信这不是医护小组的初衷,只是有需要与病人/病人家人作进一步沟通,谋求共识。